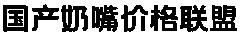最中间者为陈众议研究员
世界读书日年复一年,业已持续二十余载。这期间有反思,也有不屑;有喧嚣,亦有沉默。原因固然很多,但无论如何,阅读依然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如今,全民阅读更是时代精神的马拉松,而我们才刚刚起步。
据新近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统计,2017年我国人均阅读电子书数量为10.1种,纸质书为7.5册,虽比2016年有大幅提升,但较之发达国家和阅读大国依然差距巨大。而在近4亿的数字阅读用户中,青年占比高达70.9%,中、老年的比例分别为27.3%和1.2%。纸质阅读人群占比不得而知,估计情况恰好相反。年轻人选择电子书籍虽无可厚非,然可惜了我国先人的“四大发明”,也让我对年轻人的视力状况平添忧心。
博尔赫斯
资本和市场使人远离书本
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书是中国人发明的,他这么说是认真的。当然,他所说的书不包括泥板、贝叶和竹简,而是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物事。这个蠹书虫,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晚年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思量,天堂该是图书馆模样。”
然而,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已经繁衍出了千百万连《红楼梦》都死活读不下去的后人。因此,本文议论的不是国人的阅读数量,尽管它还少得可怜;而是质量问题,即读什么书的问题。《白皮书》没有公布国人的读物排名,这令我再次想起了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抽样调查。根据后者公布的信息,我国“四大名著”惨遭隐性“杀戮”。《红楼梦》位列“死活读不下去”榜单之首,《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也位列其中,再往下便是《聊斋志异》了。我不知道这能否代表我国的阅读现状,也不知道它是否可以代表“80后”“90后”乃至“00后”的阅读取向、审美取向。但无论如何,社会学意义上的定性定量分析并非毫无意义,全民阅读情况也并非不再堪忧。我想,夏志清、顾彬等汉学家所谓的“太啰嗦”(指《红楼梦》),刘再复先生等人的“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及周星驰颠覆《西游记》的大话戏说或许只是导致部分人等读不下去的浅层因由,而资本和市场的诱导也许才是问题的首要症结。
首先,名著从纸质到银幕或荧屏,增加的不仅是技术,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资本杠杆。譬如《聊斋志异》的一些故事被反复搬上银幕,这本该诱发人们的阅读兴趣;但其中的悖论却是影视作品先入为主,从而使人远离了书本。也就是说,倩女成了王祖贤,书生成了张国荣“哥哥”,或者《画皮》中的各色演员。文学作品一旦被影像定格,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也便不再“染指”原著了。这是现代大众传播方式、音像制品对经典阅读的最大挑战。如今,电子产品、音像制品铺天盖地,这一方面使经典的传播空间被无限放大,另一方面却大大压缩了人们阅读原著的可能性。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信息”。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吗?事实给出的答案是:经典的逻辑在影像的快速流动和肥皂泡式的飘忽中人为地褪色,并淡出人们的视界。
其次,资本与技术理性合谋,创造了无穷无尽的“奶嘴式娱乐”(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奶嘴战略”)。这些年就有无数大人和孩子深陷“偷菜”“王者荣耀”等五花八门的电子游戏而不能自拔。当然,海量的、真真假假的微信段子和各色自媒体、视频更是夺取了无数人的眼球。由是,如何让人潜心阅读,尤其是阅读经典,正越来越成为问题。
文学经典: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
读什么,尤其是孩子们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喜欢阅读,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习惯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具体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审美性于一身,且不说背后的“道”。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朴素理由。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学(当然还有艺术)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2016年,、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这个多年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的书生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这就免不了再回到经典,尤其是文学这个话题。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道出了许多好处,却始终没有明确指认何为经典。自然,反过来说,经典的好处本身成就了经典,譬如它可资反复阅读,它具有多重乃至无限的阐释空间,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世界,等等。而我想补充的是:第一,经典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但主要是现时的;第二,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它是我们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转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审美观。因此,它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介质,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同时,在民族和外国经典之间不存在排中律。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照样可以使我国读者热血沸腾,让无数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民族救亡。有关例证多多。
换言之,文学经典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精神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以柯尔律治般的假设问及邱吉尔,,他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要。当然,这非常文学,他的答案分明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经典的重要、传统的重要。而语言文学永远是一个民族所能传承的最大传统,也是其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当然,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前面说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小说可以使无数中华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问题是时移世易,如今连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那么我们还剩什么?是脱离现实的玄幻,还是无病呻吟的自恋?或者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后者并非一无是处,但若置于彼时彼地及其历史语境,那么其分量不言自明。
全民阅读变迁及现状反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孔家店和“四书五经”被五四运动的先锋们打倒,我们经历了几次翻烧饼式的大反复。早先,鲁迅取法“拿来”,并说文学最不私利。他身体力行,阅读、介绍了大量东欧文学、俄苏文学,等等。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们鲸吞式阅读和借鉴世界文学,尤其是文学和周边国家文学:从日本到、从到……
,我国遭到国家的全面封锁,文坛风向标迅速改变,我们全面学习苏联、追随苏联、照搬苏联。,苏联文学一直是我国文坛的不二选择。尽管随着“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我们也曾一度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但我们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基本没有偏离苏联模式。及至“改革开放”,风向逆转,我们开始全方位学习: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我们几乎来者不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的经典谱系和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即使来自远方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广义上也是经典谱系的组成部分,因广受推崇而辗转来到我们面前的。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何吸收文学成果,却是另一个被业界众多同人反复探讨和言说的话题。
如是,我们的文坛鱼龙混杂,气象混沌。时至今日,有些作品如《芳华》,在怀旧的面纱下锋芒直指大多数国人。以此反观作者的其他小说或影视剧本,无论是《小姨多鹤》还是《金陵十三钗》,天使皆异国“他者”。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遗孤,还是美国流浪汉,关键时刻皆成“天使”、皆能“救世”。如果不是其他编导有意加入些许暖色调(如《金陵十三钗》中的中国狙击手),我等情何以堪?同时,随着《小时代》系列的走红,大量似是而非的生活情景和时尚男女(俗称“小鲜肉”)闯入受众视域。同理,一拨拨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小仙灵”在纸上纸下、银幕荧屏招摇过市。于是,神怪出没,“耽美”成风,“女同志”充斥,却美其名曰“二次元审美”。于是,文坛正在变成游乐场或股票市场,现实主义的锋芒被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被淹没了。
这自然是大千文坛的一个侧面。但若遥望周遭,我们能说不是村上春树战胜大江健三郎、阿特伍德战胜门罗吗?这是就市场天平而言,但正因为市场天平的倾斜,才更需要学术评价、学术良知。翻检近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和治学范式,当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世界文学巨匠是如何被“淡出”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乏人问津,就连我们自家的“鲁郭茅、巴老曹”也在不知不觉中让位于张爱玲、周作人们了。这并不是要否定后者。在和平年代,张爱玲、周作人们无可厚非,但若将其置于彼时彼地历史语境,那么他们断然不应是中国文学史或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流、楷模。
而今,抑或永远,读什么、不读什么,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面前绝对是一种零和博弈。哲人叔本华的名言是:“好书让人变好,坏书让人变坏。”这与塞万提斯的说法不谋而合,后者的名言是:“读什么书,成什么人。”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二为方针”,努力建构符合我国国情,。后者必须遵循“三来主义”,,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便在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构建最大同心圆。往期图文链接:
陈众议:读什么书 成什么人
陈众议、高照成 | 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